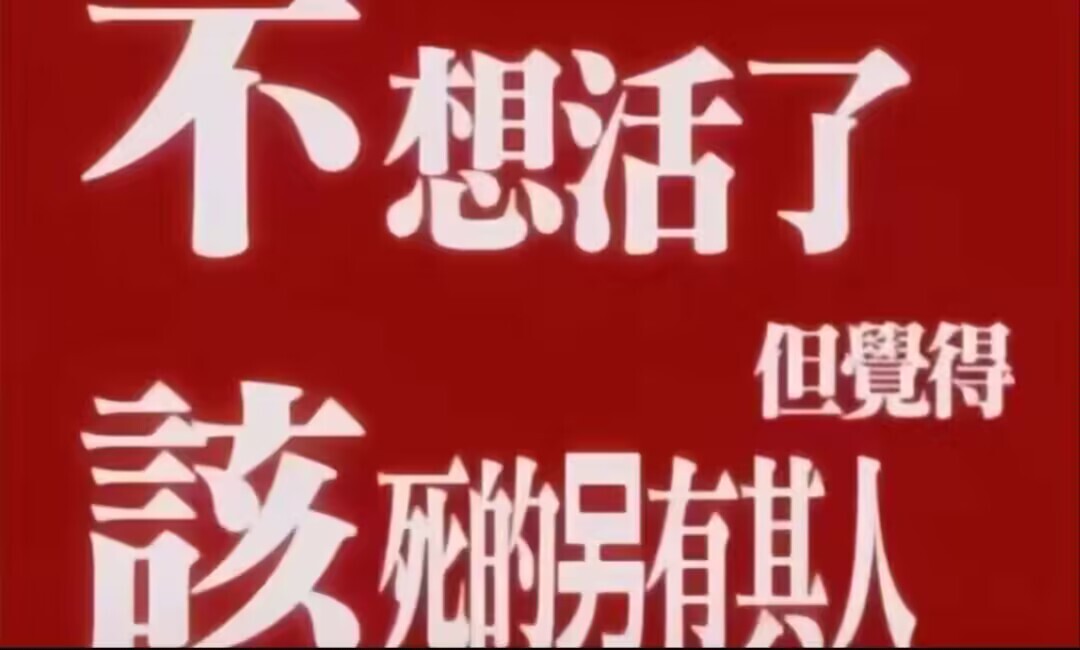
花京院在國中的時候常常流連在音像店。父母共働,自己是回家部。他並不想面對空無一人的門廊、客廳、廚房、臥室。他聽過一首算得上老的歌,California Dreaming,在暢銷區。那個時候他不在乎歌詞,往往衹是掛在耳邊,然後去隨便做些別的事情。國中的後半,他不再聼民謠,或者冷戰最為激烈的年代的任何流行歌曲。10年後他第一次認真地去聼,是在高速路上,從華盛頓到紐約去。他接到承太郎的婚禮請柬,並沒有讓自己有什麼情緒。逐字逐句地複述歌詞,才終於有了移情的方向。這是晴朗的一天,東部時間下午兩點。新人已從波士頓的大學城到達新郎家的主家,但願沒有人想到他。然而他卻無法自控地想到另一個下午,在中國南海,或者印度洋上,他和承太郎談論瑞利散射,談論沙漠。對未來的期待潛在閒聊之下,就像他曾經明明不懂歌詞卻隨著旋律起舞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