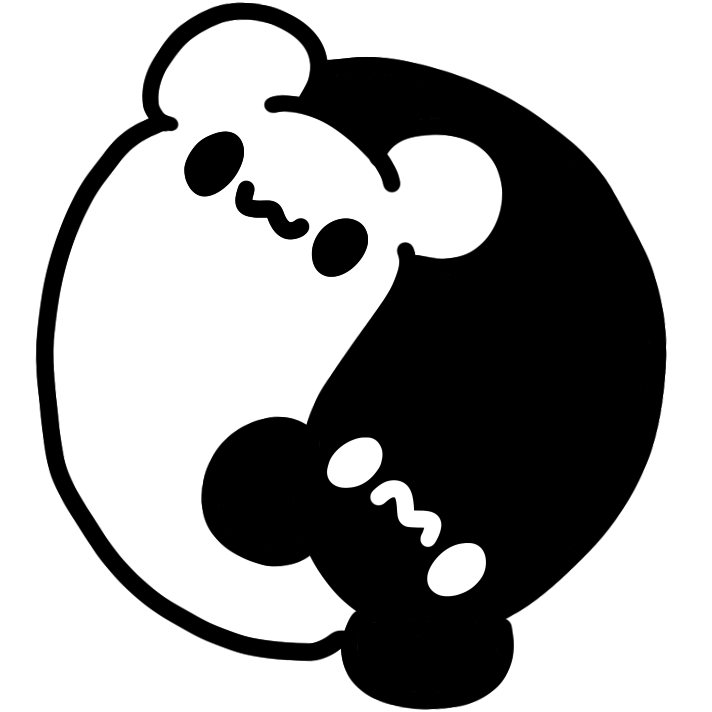問題在於他們身上的符碼是他們自己有意爭取、維護、貼上的,這些符碼是他們用來構成自己的一部分,並不是說今天我們隨意抓一個很紅的樂團來塑金身。心疼他(們)被釘在十字架上的不合理,但最一開始是他們主動走上去的啊(⋯)
雖然我也是在反省到底這種期望的界線該到哪裡,以及(出於不是本人們無法論斷的)各種原因自主背上符碼的他們又該負責到哪裡⋯
我完全能想像現場整個rundown下來最後聽到Paradise接倔強是什麼心情⋯而且他們的Paradise是刻意少唱了一個字的,本來beyond的Paradise是溫情很多具體地寫給某個對象的,但他們的不是啊⋯風華正茂年青混著夢想的他們在切格瓦拉的視覺裡唱〈摩托車日記〉「無垠的大地種不出一個夢⋯誰願意和我一起寫一個傳說」,從孫悟空唱到阿姆斯壯唱到約翰藍儂再唱回自己的夢想,在兩首小事裡邀請每個人一起做一點事情就可以震動地球,再唱〈晚安地球人〉「血液不綠也不藍⋯ 那一年大逃難⋯終於人們發射了飛彈⋯」,終於唱出Paradise+倔強,「可惜我們的故鄉,放不下我們的理想⋯最美的願望,一定最瘋狂」。天時地利人和的狀態配合演出本身的張力,我想沒有人看了那樣的演出會不被那樣的理想打動⋯
臨老入花叢是集各種歧視大成的一個詞耶(⋯⋯⋯⋯⋯⋯